近期上海财经大学钱逢胜性侵事件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反响。性侵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社会问题,很多文学作品中都对此有过描写和探讨。阅读这些作品,对于性侵受害者的精神状态以及施害者与受害者之间不平等的关系,我们能获得一个更感性也更鲜明的理解。我们挑了其中几部推荐给大家。
 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》
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》
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》是台湾作家林奕含的代表作。故事分为两条线,一条有关家庭暴力;另一条有关性侵,是少女房思琪“失乐园”的故事。她尊敬、仰慕语文教师李国华,然而李国华却是一个侵犯女学生的惯犯,文学只是他用来猎获女孩的工具。被侵犯后,房思琪找不到人倾诉,甚至得不到最好朋友的理解。羞耻与顾忌成为李国华肆无忌惮的理由,也成为房思琪的精神崩溃的原因。
乐园是李国华的乐园,对于房思琪而言,乐园只是地狱充满修辞性的伪装,是李国华利用房思琪对文学的信仰编造的一场“艺术的巧言令色”。她不得不接受这一“修辞”,因为真相太过沉重,她会被压垮。于是房思琪说: “我要爱老师,否则我太痛苦了。”
林奕含的语言风格很好,主语的故意省略、离奇的意象比喻、短语式句式的排列,都营造了一种与现实间离,但情感密集,敏锐、直觉,富有画面感的文体特征。
每个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,并不只是为了同情或者谴责,或是欣赏修辞的精妙,而是让“健康”或“正常”的我们看到人生被侮辱、被毁坏的可能性,并且警惕我们所处的位置,我们是否也像故事中那些麻将桌上谈笑邻里八卦的大人一样,成为了现实“暴力秩序”的某种同谋?
 《黑箱:日本之耻》
《黑箱:日本之耻》
《黑箱:日本之耻》是由日本自由记者伊藤诗织根据自身经历写成的非虚构作品。如果说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》通过巧妙的修辞、感性的心理描写揭开性侵受害者承受的痛苦和施害者的恶,伊藤则用更为冷静的文字还原了她遭遇性侵、诉诸法律、上诉被驳回、遭遇舆论暴力的全过程。在她的记录中,我们能看到权力者行恶的肆无忌惮,日本社会司法系统、调查机构的诸多问题,以及大众社会对于受害者同理心的缺失。这些情况,同样可以供我国社会借鉴。
伊藤诗织是日本首位以公开长相和性命控诉性侵的女性,她在书中叩问日本处理性侵案件时出现的诸多问题,审问日本社会对于性侵事件的麻木态度。更为重要的是,她用行动向同样受到性侵的女性表明,除了沉默之外,也可以有反抗的权力。她的发声获得了积极的反响,伊藤诗织事件之后,日本在更多地区建立了强奸危机中心,法律也做了部分修改。
 《黑箱:日本之耻》已经由英国BBC拍摄成同名纪录片,豆瓣评分9.1
《黑箱:日本之耻》已经由英国BBC拍摄成同名纪录片,豆瓣评分9.1
 《追风筝的人》
《追风筝的人》
与上述两本书不同,《追风筝的人》是一个关于救赎的故事。阿米尔出生在阿富汗一个富人家庭,是普什图人,阿米尔与家里仆人的儿子哈桑是好朋友,在一次风筝比赛中,哈桑被一群普什图族的孩子强暴,阿米尔目睹了这一切,但由于怯懦没有挺身而出。这之后他无法再面对哈桑对他的关心和忠诚,甚至设计赶走了哈桑。阿富汗战争后,阿米尔逃往美国,哈桑则被塔利班人以种族歧视为由枪毙。阿米尔怀着对哈桑的愧疚收养了哈桑的儿子索拉博,并试图温暖他的心。这不仅是对于哈桑的回报,同样是对他年少时的怯懦和自私的救赎。
《追风筝的人》并不直接关注性侵,性侵也不是发生在异性之间,但同样反映了性侵事件背后的权力不平等。哈桑是哈扎拉人,信仰什叶派。阿米尔以及性侵哈桑的阿塞夫都是普什图人,信仰逊尼派。在当时的阿富汗,普什图人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,哈扎拉人则地位较低。什叶派与逊尼派是伊斯兰教的两个派别,有着历史悠久的矛盾,比如伊朗就是典型的什叶派国家,而在阿富汗,则是逊尼派占多数。因此,这一性侵事件其实折射着背后的等级关系和宗教信仰冲突,哈桑作为被侵犯的一方,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,几乎不可能得到什么公平的结果。
 《冬将军来的夏天》
《冬将军来的夏天》
这本书被冠以“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》姐妹篇”的宣传语,实际上却不尽相同。《房思琪的乐园》给人一种无处不在的绝望感,《冬将军来的夏天》则讲述了绝望后的希望与慰藉,是一个“如何走出房思琪”的故事。
就像小说开篇第一句“我被强暴的前三天,死去的祖母回来找我”给人的感觉那样,这是一个带有一点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故事。故事主人公黄莉桦在一次酒会上被人性侵,母亲又为了钱将她背叛抛弃。这时她死去的祖母和四个“死道友”敲响了她的门,带她离开家。五位老人和黄莉桦都有属于自己的苦难,他们在路上互相帮助,彼此聆听,这是一条爱与被爱的路,也是一条寻求解脱的路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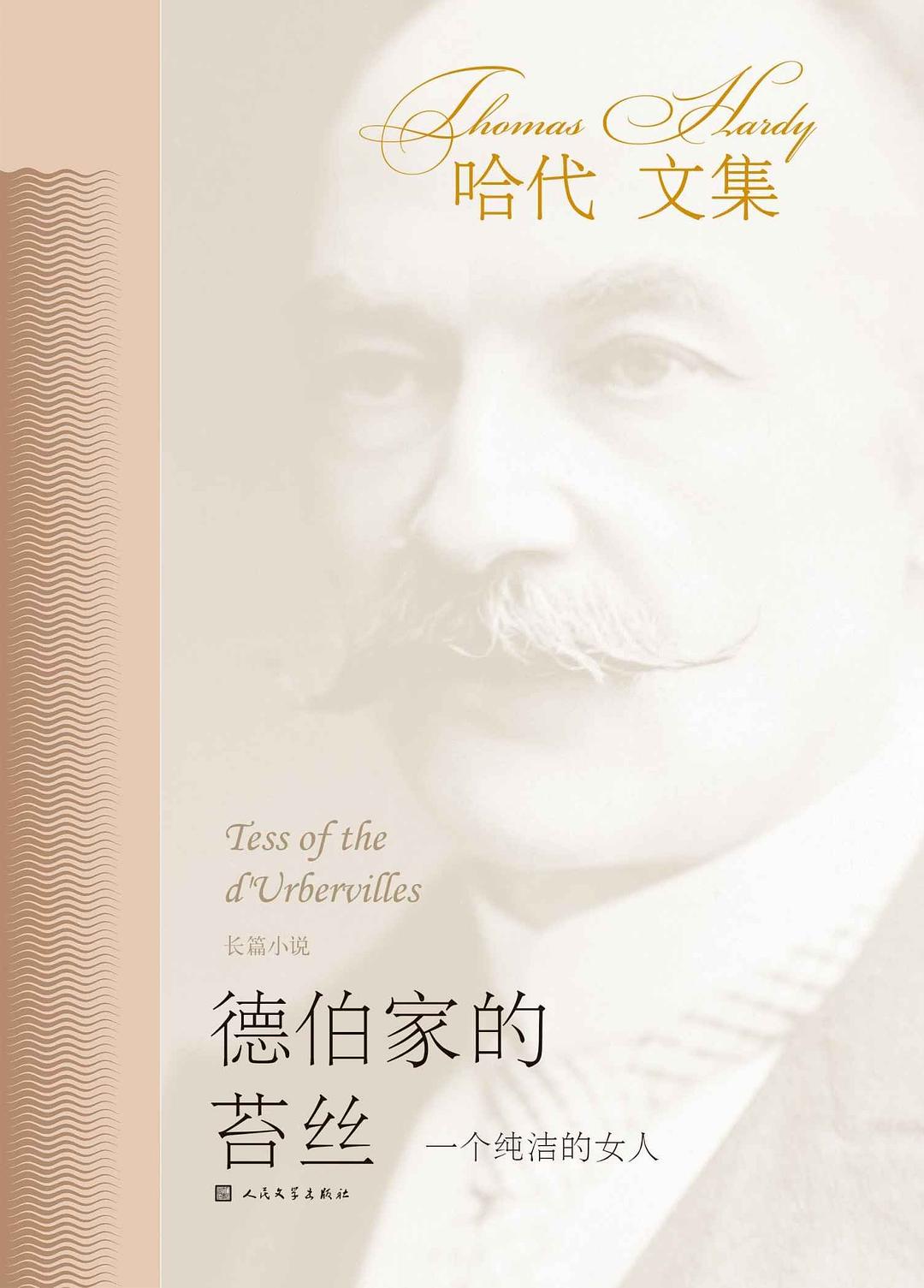 《德伯家的苔丝》
《德伯家的苔丝》
《德伯家的苔丝》是英国作家哈代的代表作。主人公苔丝出身贫苦,但她的父亲爱慕虚荣,故事的开头,她的父亲发现自己是古代贵族德伯的后代,于是派女儿苔丝去亚雷家中攀亲戚,亲戚没攀成,反而使得自己的女儿被亚雷强奸。这成为了苔丝悲剧的来源。之后苔丝与青年安吉尔相爱,新婚之夜,克莱发现了苔丝的过往,他不原谅苔丝,离家去巴西发展。苔丝沦落到农场打工糊口,又再次遇到了强奸他的亚雷。此时苔丝的父亲去世,迫于生计,她不得不与亚雷同居。安吉尔从巴西回国,希望与苔丝重归于好,但苔丝已与亚雷同居,悲痛的她杀死了亚雷,与安吉尔一同逃亡,最终被捕并处以绞刑。
在苔丝的悲剧中,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上的人对她的评价。她因为懵懂无知被亚雷强奸,甚至生下孩子(随后夭折),威塞克斯周边的居民们并不指责亚雷的兽行,反而认为苔丝“堕落”、“不贞洁”,连她的父母也不同情她的遭遇。即便是形象比较正面的安吉尔,从最开始不能接受妻子苔丝的过去,到之后醒悟并感到悔恨,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,但已经太晚太晚,悲剧早已无可挽回。
结语:
阅读文学作品中的性侵,不应该只是围观一场悲伤的表演,廉价的同情也无济于事。我们应当看到性侵背后隐藏着的力量的不平等,正如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》中李国华用知识为自己建构的隐形掌控力,《黑箱》中山口敬之也正是通过一次事关对方前途的会谈,对伊藤诗织进行了强暴,《追风筝的人》自不必说,施暴者与受害者双方各自代表了那个时代等级关系中的上级和下级。这一切并不只是性侵而已,这背后有着更深的矛盾。对于性侵事件的悲伤或者谴责并不是我们思考性侵事件的结束,我们需要向未来呼唤些什么,正如《黑箱》中呼唤的法律的改变、观念的进步,《追风筝的人》和《冬将军来的夏天》中对于救赎的希望,或是《德伯家的苔丝》中对正义的反思。就像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》中说的:
“可不要只旁观他人之痛苦,好吗?”




